快递与外卖写作, 已然成为出版界时尚?
摘要:比如她写到离开故乡,除了理想、经济等因素,还有一个原因是身为离异女性,“承受不了村里人暧昧不清的眼神”。

一本记录女外卖骑手的新书出版,改变了作者王晚的生活。她写作多年,在此之前不被出版界、文学界所重视。早在19岁时,她辍学开始北漂,从事过餐馆服务员、电话销售、网络推广、记者采编、保洁主管等职业,共计17份工作。
2024年,王晚正式成为一名外卖骑手,她把这一年的见闻写进《跑外卖》这本书,经朋友兼小说家孙一圣投递出版机构“铸刻文化”。短短半年后,王晚受到了如潮关注。她出席各项文化活动,新书入围了多个榜单,有望成为2025年最受瞩目的一本中文非虚构。
此情此景,颇像近两年来凭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一书爆火的胡安焉。这本书出版两年内畅销上百万册,售出多个语种版权,胡安焉因此暂时告别了经济上的窘迫。
同在2024年,学者孙萍和陈龙先后出版了关于外卖题材的专著。在出版业整体遇冷的当下,快递与外卖写作成为最火的类型,也让一些劳动者改变了命运。
当一名山东女性回京跑外卖
2024年春节,假期刚过一半,王晚坐上山东聊城观城到北京回龙观的大巴车。物业公司领导需要她顶岗,她回去可以拿每天200块钱的红包。
这一年,她正式成为一名外卖骑手,而父母并不知道女儿的选择。在她的故乡,如果一名女性不结婚、生育,不去做教师、公务员这类父辈眼中的“正经职业”,她就很容易成为乡人们嫌弃的对象。王晚当时离异,独自北漂,不回故乡,其一是家乡没有对口工作,其二就是要远离这样的声音。
王晚最初没有想到《跑外卖》这本书会火。她热爱写作,经常一天写上三四千字,无论从事什么职业,她都会把写作继续下去。对她来说,写作与其说是意义,毋宁说是一种本能,写出来,心里淤塞的地方就会疏通一些。
此时,胡安焉出版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已经畅销上百万册。他是一名广州普通家庭出身的写作者,先后做过服务员、外卖员、保安、杂志美编等19份工作。2020年3月,一篇记录夜班理货员生活的文章,推动他的写作得到空前关注。仅仅这篇文章收获的赞赏,就超过了他此前十年所有豆瓣作品收入的总和。
以此为契机,读库、浦睿文化等出版机构先后向他约稿。2023年,胡安焉的首部非虚构集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出版,集结了他关于做分拣员、送快递等工作感受的写作。
近年来,以外卖员、快递骑手为代表的“身份写作浪潮”,涌现出不少佳作。学术界也有《过渡劳动》《数字疾驰》这样的研究专著。珠玉在前,《跑外卖》还能否带来新意?王晚用实践证明,外卖题材并未被挖掘殆尽,基于女性肉身体验的参与者视角弥足珍贵。
《跑外卖》提供了女性视角下的外卖骑手生活纪实,蕴含了不少女性感同身受的内容。比如她写到离开故乡,除了理想、经济等因素,还有一个原因是身为离异女性,“承受不了村里人暧昧不清的眼神”。她的父亲觉得离婚是丢人的事情,很长一段时间不好意思出门,怕人家谈起女儿的婚姻。
当她跑外卖时,看到女骑手遭遇性侵的新闻,她会比男性更加心有余悸。曾经她做保洁时,同宿舍的保洁阿姨就告诫她,上门不能打扮好。她也要担忧夜宵时间段,因为有的夜宵一跑就得到凌晨一两点,对一位女性来说并不安全。
身为女儿,王晚在农村没有属于自己的宅基地。家里可以分配的三座宅基地,分别给了她的父亲、大哥、二哥。家在男人和女人的口中,是不同的含义。在北京,她也会思考“家”这个词。有一回,她把租房说成了“我家”,朋友问她,你是本地的?她连忙改口。在朋友的概念里,“家”意味着落地生根,有家人守候。就这样,这么多年她来回奔忙,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租的地方。
《跑外卖》既是在写外卖行业,也是在写一个女性游走于成长之间的身心震荡。王晚说,她既不能安闲地待在农村,也无法适应城市的节奏,“就像是夹在城市和乡村缝隙里的果子,无论在哪里长都会变形”。
这本书从作者2024年春节返京写起。王晚事无巨细地记载了成为骑手、在城中村生活、遇到难关、习惯外卖圈黑话、跑外卖高峰期等经历的感受。
她直言,由于学历、年龄等原因,决定跑外卖前还投过上百份简历,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单位邀请她面试,开的工资大部分比她入行时还低1000元。哪怕是月薪5000元的保洁主管,要求都比从前高。
在她的笔触下,低薪工作中低自尊的处境被直白展现。管理者常常使用贬损人格的语言,来斥责下属的工作失误。比如在她做保洁时,有一次主管要她叫2C区的保洁阿姨,她新来不久,对区域不熟悉,不小心在群里“艾特”了2B区的保洁,主管对她说:“我看你就是个2B!”
跑外卖,相当于她重新感受了一遍北京。她见识过同时开两三个店的商家,却只挂一个招牌。某骑手之前给工地安装电路,一个月能赚一万多,后来很多工地都不开工了,他在2023年给某工地做的一份活儿,到现在都没结工钱。
频繁送餐也让她发现,北京有一些基础设施做得并不合理,部分过街天桥没有专用坡道。有一回,她上天桥时出了意外,车子砸到腿,手上的焖锅外卖洒漏了一点汤汁到鲜花外卖上。那束花要四百多块钱,她担心赔付,想找个超市买把剪刀,将有汤汁的那几个花边剪断,但快到送餐点都没碰到一个超市,她迫于无奈用牙把花边给咬断了。幸亏顾客没有追究她。
她也认识一个迫于生计跑外卖但心底里抵触这活儿的人,此人经常吃到罚单,理由多是“态度不好”,他跑外卖又故意让自己收到罚单。王晚写道:“他好像被困在他的愤怒里,就像陷入沼泽地一样,越是用力挣扎,下陷得就越快。”


王晚和她写的《跑外卖》。
外卖骑手固然辛苦,但王晚见识过太多和这一样辛苦、工资更低、缺乏保障的活儿。比起跑外卖,她更厌倦回到那些工作中,她也害怕失业。待业时,她每次付款买东西后,都会很快退出付款页面,更不敢去查自己的账户余额。
王晚的语言活泼辛辣、率真坦荡。她写城中村的路,“被截得跟狗吃屎一样”。写在别墅区送单:“那些设计得弯弯曲曲的道路,可能是为了给业主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,但对我来说毫无必要。”她写高峰期送餐,“就像拎着哑铃跑操”。
她同样写到了逆行、数字控制、外卖骑手缺乏保障等问题,但并不是以纯粹批评的态度来回顾骑手生涯。她说:“尽管时间支离破碎,身体日渐磨损,我却感到安心,因为有这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,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。”
他努力做到尽责,害怕受到打击
王晚的写作,适合与胡安焉的作品对照阅读。在种种限制中,他们努力搭建自主的可能性。通过写作,他们让更多人发现,自己的处境不是个例。
王晚的写作,兼具女性和体力劳动者的双重视角,聚焦于外卖工作。而在胡安焉的写作里,送外卖和送快递都只是其中一环,他更像是一个人生的体验派,以自我为方法,去书写一个当代文青、游民、无保障劳动者的精神动荡。
胡安焉希望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,不必为此和厌恶的现实打交道,但经常事与愿违。他自述:“我很清楚自己的写作,从最初就怀有一种逃避的动机。比如说,躲到想象和虚构中,而不是活在现实生活里。”
许多媒体会将胡安焉作为“底层劳动者靠写作改变命运”的典范来书写,准确来说,胡安焉首先是一名创作者,其次才是那些职业的参与者。他早在2010年左右就在文学论坛“黑蓝”发布小说,参与大量文学讨论。他在送快递前10年,就拥有了身为创作者的自觉。但是,他的前期写作不被主流文学杂志认可,无法带来财富累积,这使他渴望纯粹的创作自由,又限于物质困窘。
胡安焉的生平,颇能代表许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写作者。他于1979年出生在广州细岗,1984年搬到中山大学对面,一家六口——外公、外婆、父、母、姐姐和他自己,住在一套56平方米的单位宿舍。胡安焉的母亲是上海人,1950年代初移居广州;父亲是客家人,出生在广东省陆河县。
2017年,胡安焉在顺德陈村枢纽中心担任夜班理货员。2018年,他到北京通州入职S公司,从事快递投递工作。同年9月,他跳槽到了唯品会自营的品骏快递,直到2019年11月品骏快递结束运营,他和所有同事被公司遣散。
他长期生活在缺乏保障、飘摇的生活里。在主流话语里,他显然不是一个成功案例。吊诡的是,他以底层劳动经验为养料写作的书,反而成为城市中产、文科从业者、主流媒体都纷纷关注、投射同情的对象。当出版物跃升为年度畅销书,胡安焉成为各大文艺活动的座宾,在世俗眼里成为一个励志的典范。
这背后暧昧的逻辑在于,无论写什么,只要成为爆款,成为知识精英认可的商品,过往的种种痛苦都能在成功学叙事中化身为“必要之条件”。但如果胡安焉的写作没有成名呢?事实上,在他成名前后,他并未发生本质改变,外界给予的目光却已天差地别。当“底层写作”成为城市中产最喜爱的类型之一,围绕其所展开的成功学叙事、身份固化叙事,仍然值得读者审慎判断。
身为创作者,胡安焉亦明白这点。他在多个场合表示,自己深知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成功有运气因素,他警惕自己被当做一个样板化的底层,一个被他人庆祝同情的“底层写作者”。比起非虚构,他更喜欢写小说,希望人家用严肃写作者的标准去要求他。他直言自己接下来的作品会是虚构,哪怕知道继续出非虚构能挣更多钱,但他不想掏空自己的经验去进行一次次套路化的写作。
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最有趣的一点,恰恰是那些老实、朴拙、有点冷幽默的表达。比如他说,自己之所以写作,是因为写作这件事不花钱。他在工作中努力做一个勤奋而尽责的人,害怕受到打击。而他送快递、做分拣员,哪怕从中收获经验,也不会为此赋予抒情的、崇高化的表达。
他经历过贫穷,不想美化贫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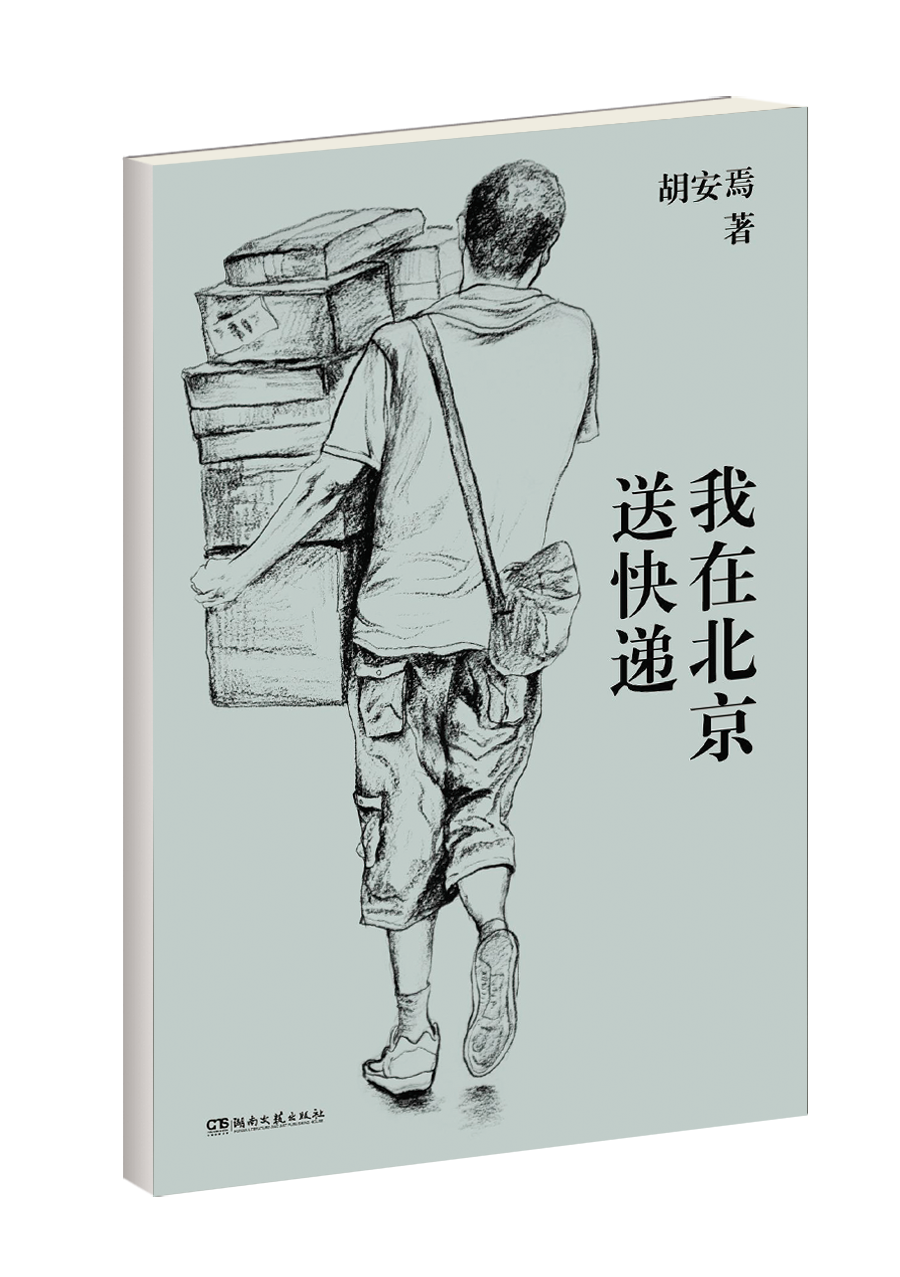
胡安焉和他写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。
学者视角下的外卖骑手研究
如果说胡安焉和王晚的写作是基于个体经验,学者孙萍和陈龙基于大量调查、数据分析的研究,则为读者理解外卖行业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抓手。
2010年以来,平台经济和“零工潮”业已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现象,外卖骑手是其中典型的群体,它诞生于中国平台经济兴起的阶段。因为美团、饿了么等平台打通的线上与线下送餐服务,外卖骑手穿行于城市森林,从不被人了解,到成为被苦情化叙事的对象,再到成为影视、文学作品常常书写的群体,外卖骑手是城市里最常见的群体之一,却也被不同叙事赋予了不同的色彩。
近年来,关于外卖骑手的写作数量颇多,但要做到写出新意也更难。陈龙的《数字疾驰》与孙萍的《过渡劳动》,是目前“骑手研究”最有说服力的两本。
陈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,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劳动社会学,包括数字经济、平台劳动管理与企业劳动关系。他是最早研究外卖骑手的学者之一。2018年,他加入北京中关村外卖骑手团队,进行了为期近半年的田野调查。早在2020年,他就发表了《“数字控制”下的劳动秩序——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》一文,在学术界引起颇大反响。
2024年出版的专著《数字疾驰: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》,就是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。这本书不但具体地呈现了骑手在平台经济下的竞争与生存策略,也用多个鲜活故事,让读者看到的不只是符号化的骑手,而是他们辛苦奔忙的人生。
陈龙这本书的重点,就是展现“数字控制”与“平台经济”如何套嵌,成为当代最有力的规训手段。在零工普遍化的处境下,这一代劳动者对于时间、空间、自由等概念的理解,出现了怎样的改变?
譬如在该书第六章,陈龙展现了骑手行业内卷化的过程,外卖平台公司研发的订单调度系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。
第一阶段是“人工派单”,订单主要由后台人员派单,效率低,骑手一天也就跑十几二十单,挣的不是很多,但相对没那么卷。
第二阶段,骑手抢单,谁离得最近或者谁顺路就去抢单,全部订单改由平台系统负责收集、发布。
第三阶段最关键,人工智能派单。平台建立大数据系统,通过算法进行智能派单,人工智能和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发挥关键作用。在理想情况下,智能派单系统考虑的因素既包括商户、时段、天气、出餐历史、速度、餐盒包装数量、骑手的负载量、骑手的配送速度等因素,还包括顾客期望送达的时间、订单的金额、订单的导航路线、订单的重量和体积。但这只是理想状态,现实中骑手依然会面对送货所需时间比预估长,为了避免超时而不得不选择逆行。
这一阶段,外卖行业被广大群众认知。在经济调整期,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、待业人士也加入了外卖行业,加剧行业内卷化。
与此同时,被优化的平台不仅规划了骑手的工作,也监控着外卖骑手的整个送餐过程,将实时情况传送给站点和顾客。作者引用了法国思想家福柯对于“全景式监狱”的阐述,一针见血指出,平台与骑手的关系就像是瞭望塔与囚犯。这座瞭望塔就仿佛全天候展现控制欲的家长,它看见骑手开小差,要求骑手按照最优路线行驶,也会在骑手生日时送上祝福、离别时送上谢语。在人类的研发下,平台成了最精明的管理者,也是最冷酷的监工。
由此,作者引出他最关心的议题——“数字控制”。本书写道:“不同于工业化生产时代的简单控制、技术控制以及科层控制,平台经济时代的资本控制以数字控制为显著特征。”数字控制深刻改变了全世界的用工模式和生产方式,外卖行业只是冰山一角。外卖骑手的处境,是当下数字劳工的一个缩影。相比起前互联网时代,数字控制是一种更隐蔽又强势的控制,平台看似营造了自由的氛围,部分骑手理论上成了自由职业,但他们实际遭受的控制感并没有变轻。
外卖公司通过数字平台,淡化了自己的雇主身份,又通过顾客评价骑手的设置,加剧了骑手与顾客之间爆发矛盾的可能,将传统的劳资关系矛盾转嫁为平台、顾客与骑手之间的矛盾。
陈龙并没有将平台与骑手的关系,书写为单纯的控制与被控制。在“下篇”部分,他也展现了骑手面对新形势所做出的巧妙应对。比如入行久了的老骑手,擅于通过“报备”存在的漏洞来弥补“挂单”浪费掉的时间。
所谓报备,原本是为了应对餐厅出餐慢的情况。当指定餐厅出餐慢时,系统允许骑手通过“报备”延长送餐时间。但骑手“报备”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:在餐厅附近;到店5分钟以上;餐厅在预计时间没有出餐。在这三个条件里,2和3都是有操作空间的。比如骑手其实已经拿到餐了,但他为了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富余,就报备来延长时间。只不过,当这种方式被更多骑手效仿,平台也会想出办法来优化系统。《数字疾驰》呈现了平台与骑手之间的隐秘较量,它不是一种明面上的激烈对抗,而是迂回的斗智斗勇。
外卖骑手是当代劳动者的一个缩影
这种迂回较量,在孙萍的《过渡劳动》中亦有体现。比如一位当时在北京房山的外卖骑手,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远程切换账号的系统漏洞,通过微信群告诉房山区的众包骑手,让他们集体抢单、相互捎单,以此提高工作效率。好景不长,等平台修补了这个漏洞后,相关骑手的账号也被关闭了。


陈龙侧重于对“数字控制”的分析,而孙萍拓展了对女性骑手的呈现。她采访了30位女骑手,发现有27位来自农村,3位来自城市,超过三分之一的女骑手表示到大城市是因为丈夫也在这里打工。她们之所以跑外卖,是因为“找工作困难”,外卖来钱快,不容易出现拖欠。
此外,有近三成女骑手是因为离异、家庭变故等原因而外出跑外卖,这与王晚的《跑外卖》形成呼应。这些女性受到乡土社会的困扰,当她们最初跑外卖时,心理上仍伴随着羞耻感与自我蔑视。外卖领域的“男性审视”,男人们对她们的说教,也会加剧她们的自我贬低。有的女骑手选择承受孤独,哪怕显得不合群,有的人则学习男性骑手的话术,与男性打成一片。为了提高效率,聪明的女性骑手有时候会选择“示弱”策略,利用男性对她们的刻板印象,帮助自己生存下来。
在快速流动的城市森林里,女骑手也在寻求社群的组建,给自己一个“说话的地儿”。在群里,她们以姐妹相称,如“大姐”“小妹”等,会在里面分享自己的定位、订单截图,也会聊养生、育儿、美容等话题。
《过渡劳动》与《数字疾驰》的优点,都在于大量实例与调研的结合。比如在《数字疾驰》中,陈龙对北京多地团队骑手和众包骑手进行了问卷调查,最终收到有效问卷200份。他自己进入骑手团队后,也放下学者姿态,积极混入他们之中,熟悉他们的生活门道。孙萍的调研小组则涉足北上广在内的十几座城市,在东北、华北、华中、华南、西南地区都有样本。
《过渡劳动》另外写到一个有趣之处,叫做“养系统”。即系统通过数据积累来对骑手进行等级评定和派单,骑手需要坚持跑单,摸索出更好的策略,才有机会“弄好自己的数据”。如此一来,送单多、时效快的骑手会得到更多的订单,而单量小、“挑单子”的骑手就会被系统边缘化。
王晚在《跑外卖》中也提到,骑手们对“单王”又爱又恨。她知道“单王”努力增加收入无可厚非,但“单王”不断提高效率,系统又以“单王”表现为依据,压缩送货时间,迫使其他骑手也要加入这个疯狂透支速度的游戏中。
孙萍说,自己无意去迎合、强化主流的常识性问题,也不想简单地批判“资本万恶”,而是希望通过研究去推动骑手职业环境的改善。在这一点上,她与陈龙不谋而合,都在跳出二元对立叙事,呈现零工经济、数字劳动的真实图景。
2025年,胡安焉已步入人生新阶段。首作畅销,让他坦言至少未来十年里养活自己应当不成问题,因为他物欲不高。王晚则奔波在宣传新书的进程中,继续探索自己的道路。她的书中有动人一笔,2024年春天,她更具体地感受到树叶是怎么一点点绿起来的,花是怎么开的,送完单子后赶到河沟,在河边捡石头。就这样,她的屋子里摆了很多捡回来的石头。那是寻常的一天,但在那一天,她发现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
ABOUT / 相关报道


